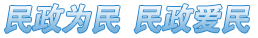多元主体 多维协作 有效提升困境儿童福利保障水平
邓 丽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培养好少年儿童是一项战略任务,事关长远”。总书记关于儿童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涉及教育改革、营养健康、医疗用药、安全风险防控、网络环境整治、婴幼儿照护、儿童早期教育服务和新时代儿童慈善事业发展等多方面,尤其格外关注、格外关心孤儿、残疾儿童、贫困家庭儿童、农村留守儿童、流动儿童等困境儿童群体的健康成长。
近日,国务院出台《意见》,坚持儿童优先发展和最有利于儿童的原则,明确保障基本、优化服务、维护权益、促进发展的工作思路,聚焦六大保障体系,提出21项创新举措,旨在精准、系统提升我国困境儿童福利保障水平,更好地维护困境儿童生存、发展和安全权益,促进困境儿童健康成长成才。困境儿童福利需求的多样性决定了福利供给必须走向多元化,而多元福利供给的实现,需要家庭、政府、社会组织和专业机构等多方主体从监护职责、制度保障、服务供给和技术支持等多维度协同发力。
■ 困境儿童福利需求的多样性
在现代社会治理视野下,困境儿童福利需求由传统物质保障向社会公共服务延伸,呈现出生理、心理、安全和发展等不同需求复合、叠加态势。回顾我国儿童福利保障制度的发展历程可知,从最初着力解决贫困儿童和流浪儿童的特殊困难,到将孤儿纳入制度性保障,进而扩及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又及对儿童入学、就医问题的系统关注,困境儿童的外延不断拓展,映射出我国儿童福利制度逐步由补缺型向适度普惠型转变的轨迹。
困境儿童的界定是基于对儿童生活境况的确认,而非对儿童内在本质的定性。这意味着,困境儿童的成长发展需求与其他儿童的多样化需求无异,只是因为其需求未获有效满足、成长未获有效支持,从而陷入生活困境。不同儿童群体的福利需求既有与其具体境况相关联的特异性,又有儿童身心发育普遍所需的共通性,如孤儿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迫切需要基本生活保障,同时他们在适龄时会有入学接受教育的需求,重病或残疾儿童需要专业医疗救治和康复服务,一旦因病致贫则需要生活救助,流动儿童面临异地就医、教育衔接等现实难题,留守儿童可能遭遇监护或照护缺失导致的安全风险等,而各种困境下的儿童都需要心理、认知和情绪方面的引导和支持以帮助其应对困境与挑战。多项研究表明,大量困境儿童同时存在两种以上福利需求,其多种需求有不同组合形式,如“医疗+教育”“心理+安全”“生活救助+教育+监护支持”等。困境儿童需求的多样性与复合性要求传统的单一、单向福利供给模式必须转向物质与服务福利兼顾、政府主导与多元协作并进,从而构建起灵活有效的福利响应机制。
■ 困境儿童福利供给的多元化
我国宪法规定,儿童受国家的保护,国家培养少年、儿童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确立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明确规定:保护未成年人,是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人民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城乡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未成年人的监护人以及其他成年人的共同责任。
作为国家责任的具体承担主体,多年来,实务部门在加强自身服务能力和工作队伍建设的同时,持续探索困境儿童福利供给的多元化。国务院于2016年发布《关于加强困境儿童保障工作的意见》,指出困境儿童保障工作应坚持家庭尽责、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分类保障基本原则;2019年,民政部等10部门和单位联合就健全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关爱服务体系发文,要求提升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和儿童福利机构服务能力,加强基层儿童工作队伍建设,并通过培育孵化社会组织、推进政府购买服务等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广泛参与;2023年,民政部、教育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联合发文,要求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部门协作、家庭尽责、社会参与,服务主体多元、服务方式多样、转介衔接顺畅的困境儿童心理健康关爱服务工作格局。在此基础之上,《意见》构建起更加宏观、更加深入的协作机制,要求通过设施建设、经费保障、激励机制等切实推进人、财、物等力量资源向基层一线倾斜从而提升基层基础服务能力,通过及时修订相关法规制度、细化分类标准、完善精准检测摸排机制、加强数据建设和数据共享等实现精准服务管理,通过有效发挥共青团、妇联、残联等群团组织优势作用、宣传强化全社会保护儿童合法权益意识、推动慈善帮扶和志愿服务等,促进社会力量参与。
■ 困境儿童福利提升的多维度
困境儿童福利保障水平的提升,需要家庭、政府和社会等责任主体在各自领域发挥功能优势,形成监护责任、制度保障、服务供给的多维度协作网络,为困境儿童构建从生存权益保障到发展能力培育的全方位支持体系。
家庭,始终是儿童成长的第一责任主体。《意见》要求通过指导、督促监护人履责以及构建普惠性家庭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强化家庭监护责任,对于监护不力或脱离监护的困境儿童,则通过民政部门临时监护和长期监护机制体现国家监护职能,并要求优化儿童福利机构转型,以充分发挥其监护支持作用。家庭监护与国家监护的衔接和优化,能够防止困境儿童陷入监护罅隙,确保在制度层面所有儿童都有对其负有法律责任的主体。
在现实层面,困境儿童的家庭监护与亲属支持往往是失效甚至缺失的,因此需要外界干预和扶助,尤其是由政府为这类群体提供主要的福利供给。《意见》要求政府通过制度创新和技术赋能构建起精准而全面的困境儿童福利保障网络。首先,通过基本生活保障标准的动态调整机制及其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统筹衔接以及医疗救助比例倾斜等实现分类施策,有助于精准识别和及时回应困境儿童的生活需求。其次,统筹推进六大保障体系建设,不仅通过生活保障、医疗康复等基础福利和服务确保困境儿童的生存权益,还从教育帮扶、心理健康关爱等方面切实保障困境儿童的发展权益。最后,依托困境儿童数据库建设和部门信息共享机制,实现从被动救助向主动发现的模式转变,且通过跨省通办、异地结算等政务创新突破地域壁垒,运用数字技术助力困境识别与福利发放。
社会力量作为政府服务的重要补充,愈益走向组织化和专业化发展路径。不仅是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本身采取组织化运作的形式,群团组织、志愿服务组织和项目实施团队的结合也将形成更加规模化的社会服务力量。基层儿童工作者和照护、特教、心理辅导、医护和康复人员等都将进一步提升其专业水平,致力于为困境儿童提供规范而有效的服务福利。
儿童福利制度是反映一国社会保障体系成熟与发达程度最重要的指标之一。《意见》致力于建构多元主体、多维协作的困境儿童福利体系,在此体系下,家庭、政府、社会通过边界划分与功能整合,广泛覆盖困境儿童群体对生活保障、心理支持、安全防护和发展赋能等方面的需求,致力于保障困境儿童平等享有足以支撑其生存与发展的成长环境,推动我国儿童福利制度向更高水平的普惠性、精准性和可持续性迈进。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副研究员)